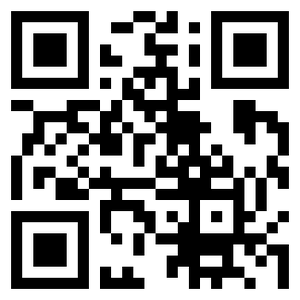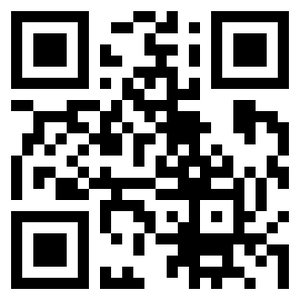1987年10月初,国家领导人陆定一刚刚结束了东北的考察之旅,返回北京后,发现办公桌上多了一封来自群众的信件。信中,寄信人自称赖章盛,一位大学教授,他在信中提到,自己认为陆定一的失踪多年的女儿陆叶坪,可能就是他的母亲华丰金服,并在信中详细列举了自己推测的依据和线索。看到这封信时,已年满81岁的陆定一情绪激动,心中百感交集。此前,他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追悼亡妻唐义贞的文章,文中提到了自己一直未能找到失散的女儿的遗憾,而赖章盛正是从这篇文章中得知了线索,进而决定写信联系陆定一。
其实,这个线索并不是赖章盛第一次接触到的,三十多年前,陆定一就曾调查过类似的情况,但因当时的种种原因,他以为自己可能弄错了,未再深入追查。然而,随着信中提供的信息逐渐浮现,陆定一的内心充满了疑虑和希望,难道真的是她?难道父女之间已经错过了三十多年?他决定再次亲自调查,一定要查个明白,否则自己一生的遗憾恐怕永远无法释怀。
展开剩余81%经过一系列的走访和查证,陆定一终于获得了肯定的答复。当他得知自己的女儿终于找到了时,尽管年事已高且身体虚弱,他仍决定不顾一切,跨越千里从北京赶赴南昌。父女二人在久别重逢的瞬间,抱头痛哭,场面感人至深,连在场的人也都泪眼盈盈。经过了数十年的煎熬和期盼,这一刻的团聚,实在是他们早已期盼太久的梦。
那么华丰金服,为什么在身居高位的陆定一,竟会失去如此亲爱的女儿?他在这几十年里为何都未能找到她的下落?这一切的答案,恐怕要追溯到陆定一与亡妻唐义贞的爱情故事。
唐义贞出身革命家庭,从小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。1928年,在党的安排下,她前往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深造。那年,她刚满18岁。年末时,陆定一也作为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成员来到了莫斯科,两位怀揣着相同理想的年轻人在异国他乡相识相知,最终相爱并于1929年12月结婚。
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,他们的婚礼简朴至极,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婚礼仪式。两人租住的小屋里,夫妻俩自制了一桌简单的中国菜招待同志们,这场婚礼虽然简单,但却充满了革命情怀。唐义贞没有穿平日里的苏联校服,而是特意穿上了那身镶金丝绒边的红色旗袍,婚礼的气氛也因此增添了一丝温馨与喜庆。
1930年夏天,陆定一和唐义贞返回上海,并在陆定一的住所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宁的婚姻生活。那时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下,党内的同志们几乎无法公开活动,为了保护自己和党组织的安全,夫妻俩尽量避免外出,每天几乎都待在公寓里。由于环境的特殊性,他们甚至不能拍一张合影,任何一张照片都可能成为敌人追查的证据。唐义贞在给母亲写信时,提到自己的丈夫时也只是称他为“陆先生”,以防止暴露身份。
尽管面临种种困境,那段短暂而宝贵的夫妻生活却成了他们心中最美好、最难忘的回忆。无论日后的相聚还是离别,那段时光都将永远在他们的心中留存。
然而,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党的任务需要,唐义贞于1931年5月受党组织指派,和何叔衡一起假扮父女前往闽西苏区工作。在1931年6月,他们在虎冈与丈夫陆定一偶然重逢。这是他们结婚一年多来,第二次见面。
随着反“围剿”斗争的胜利,他们从虎冈转移至长汀,再到瑞金的叶坪一带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在1931年12月30日,唐义贞在瑞金叶坪生下了一个女孩,为了纪念这片红色的革命圣地,取名陆叶坪。
但时局风云变幻,1934年10月,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失败,主力不得不开始长征。陆定一当时正遭受“左倾分子”的打压,暂时被派到沙洲坝编辑党刊。由于唐义贞身怀六甲,行动不便,组织决定她留在苏区继续工作,而她所在的卫生材料厂也要随红军主力迁移。
那天,唐义贞在黄昏时匆匆赶到沙洲坝去探望丈夫。陆定一看到妻子风尘仆仆,满怀忧虑。红军主力即将撤离,各种反动势力必将紧随其后,妻子临产在即,女儿只有三岁,如何安然度过这一难关,成了他们最大的担忧。
唐义贞深知这次别离将是生死未卜,她微笑着对陆定一说:“你放心走,不必担心我。我已经安排好了,把叶坪托付给张德万,他是厂里的老管理员,孩子很喜欢他,叫他‘好妈妈’。我会好好照顾自己,也会照顾好孩子的。你带着重任走吧。”唐义贞的话语坚定而安慰,让陆定一略感放心。
她未留下来吃晚饭,只是匆匆告别,离去时挥了挥手,说:“厂子里有事,我走了,你保重。”陆定一目送她离去,依然不舍,紧紧抓住缰绳,却又迟迟不肯松手。唐义贞笑着调皮地说:“刻字匠,笑一笑!”她说完这句话,轻轻挥了挥马鞭,消失在暮色中。
当夜,陆定一随着红军主力踏上了艰难的长征路,而唐义贞则用她的坚韧继续在苏区的战斗中奋勇前行。
发布于:天津市创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